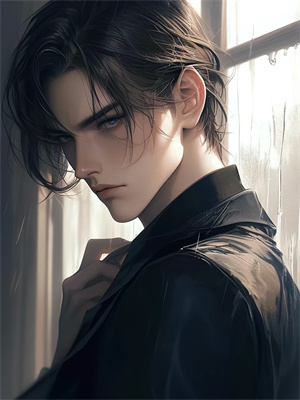简介
喜欢小说推荐小说的你,有没有读过这本《两难:咸鱼皇子的抉择》?作者“细雨湿高城”以独特的文笔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李钰李钧形象。本书目前连载,赶快加入书架吧!
两难:咸鱼皇子的抉择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太子病倒在行宫,这消息传到东宫,太子妃等人一下子就慌了神,想去行宫侍奉,但是过来传话的内侍传了太子口谕,说是让众人安心在东宫等待,不要擅离,所以众人虽然心焦,却也不敢违拗太子的意思。等了三四天,太子身子逐渐恢复的消息传来,东宫上下才松了一口气。
李钰这些天一直是上午读书,下午练字做窗课,表面上倒是有了几分用功的模样。但是他心中的震动和不安却与日俱增。太子监国的艰辛他看在眼里,可是哪怕再谨慎在用心,朝局波谲云诡,又岂是一人之力可以处理好的?
外面流言四起。虽然陆青不让别人乱给他传话,但是他有马宝儿这个“包打听”再加上李存义这个伴读,京中朝中的流言,十有八九都被他听在了耳中。无论是五溪蛮还是开中法他都不太懂,但是皇帝反复召两府宰相去行宫,后来又差点问罪太子一事,却是满朝廷传得有鼻子有眼。行宫里不过那么些人看到事情的经过,这个消息如何能不胫而走,传遍京城,思之不禁使人背脊发凉。后来又传来皇帝要整顿盐务和户部尚书出外的消息,似乎是有利于太子的,但是谁知道这不是又一个大坑呢?权力的中心,漩涡是那么多,如果踏入其中,自己又有多少把握能全身而退?
虽然李钰今年才九岁,但是九岁的皇子,的确已经不是小孩。明年他就不能再住在关雎宫,按祖制,十岁以上的皇子将不能随母亲居住,要搬到外面。为了方便皇子们读书,通常王府会安排在宫城的东北角,那边有一片宅邸,号称“十王宅”,专门供尚未大婚离京的皇子居住。这十王宅因为不在内廷,没有宫禁,人员出入比东宫还便利些,若要夺嫡结党,真是再方便不过。如果这次太子……那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放在风口浪尖之人?
李钰虽然有一个成年人的灵魂,但是作为一个尚未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,要论城府魄力,实在是乏善可陈,要论野心雄心,也是无从谈起。在“前世”,他不过想着自己能顺利毕业,找个类似出版社编辑或者政府文职人员的工作,娶妻生子,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。从来没有想过,自己竟然能有机会和权力扯上什么关系,不要说是最高权力。可是现在重活一世,上天将这样一个机会放在了自己的面前,自己是否要上前一步?
李钰最近一直在学《春秋公羊传》,一部春秋,多少弑君灭国,多少父子兄弟相残,触目惊心。他不知道若这本书真的是孔子所写,夫子在写作的时候是何种心情。人异于禽兽几希?虽然他一直知道,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混乱不堪,但是现在一点一点剖析起来,还是让人不忍直视。还记得太傅讲“郑伯克段于鄢”,这段历史被《左传》记录得活色生香,还收入了《古文观止》,他是十分熟悉的。在《公羊传》中,语言就要简练很多了:“夏五月,郑伯克段于鄢。克之者何?杀之也。杀之则曷为谓之克?大郑伯之恶也。曷为大郑伯之恶?母欲立之,己杀之,如勿与而已矣。段者何?郑伯之弟也。何以不称弟?当国也。其地何?当国也。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?在内也。在内虽当国不地也,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。”看似毫无情感和细节的几行字,内藏着比刀斧还严厉的批判。还有申生与重耳,还有隐公与桓公,数不胜数的人伦惨案,这就是权力的力量吧。以前,这些历史故事离他很远,现在有些历史人物却就像是他处境的翻版。都说以史为镜,那么他就好好读一下书吧,希望能在这发黄的纸堆里找到一条路。
这边李钰在思考前路,那边李钧则在积极备战。作为太子,他没有时间悲春伤秋,因为当他被立为太子的时候,他就已经没有了退路,历来太子,不是登位九五,就是被杀被囚。或者应该这么说,当他作为嫡长子出生的时候,就没有了退路。
虽然还在行宫,但李钧还是下令搜集了有关于盐税的各种资料,包括历年盐引发放的数量和盐税征收的账册,虽然这些他都已经看过了,但是他想再细细地看一遍,也许能发现一些问题。他还召见了以前在盐道任职过的官员,让他们给自己介绍情况,剖析可能出现的漏洞。甚至以前在两淮当过地方官的人,只要现在还在京城的,他都找来问过了。虽然不敢说这些官员说的都是实话,但是一下子找来三四十个官员分别问话,李钧就不信,他们都是铁板一块,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。再加上现在天心在自己这边,下面的官员也不敢随意敷衍。
短短五六天的时间,李钧就大致摸清楚了盐税减少的原因,和他之前想的差不多,一是私盐贩卖逐渐猖獗,二是盐引来路过于复杂导致管控难度大。这两条都是明面上的,但是深挖下去,还能牵扯出不少东西。比如私盐贩卖,这一贯是朝廷严厉打击的对象,贩卖私盐十斤以上就要杖责,百斤以上直接是流刑甚至斩刑,各州刺史和按察司都受命严控私盐,但是私盐还是一年比一年多,这其中的问题不言自明。
明天皇帝就要回銮了,李翊已经把查盐税的事,全权交给了太子李钧,让他便宜行事,拘问三品以下官员不必请旨,太子教令等同于皇帝敕令。这么大的权柄,自然也意味着非常大的责任,李钧将第一次真正地独立面对官场,那个上下勾连,有无数潜在利益交换的地方,人人看上去都是饱读诗书,正色立朝的国家栋梁,但是暗地里,心肝肺腑是什么颜色,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。
皇帝李翊这时正坐在澹宁斋内,周围的内侍宫人进进出出收拾东西,看上去十分忙碌,他看了一眼身边的王忠,说:“你说,朕明日到底要不要回銮?第一次让太子放手做事,若朕在身边,他不免束手束脚吧?但是若朕不在身边,还真有些不放心。”
“前朝大事,老奴岂敢置喙。”王忠恭谨地说。
“这里又没外人,常侍何必藏拙呢?”皇帝笑了一下。
“陛下回銮,当可镇住宵小之心,毕竟太子还年轻,威信不著。且若陛下在行宫,殿下在京城,虽不远,沟通音讯却也要一日半日的功夫,万一有人离间天家父子,则事不谐矣。故而,依老奴愚见……陛下还是回京比较好。”王忠认真地斟酌着词句,向皇帝禀告。其实他心里清楚,自己这位陛下,最是多疑之人,可能是因为自小就被各种逼迫猜忌,养成了谁都不信、谁都不靠的性子,太阿权柄只可在自己一人之手,所以皇帝是不可能不回去的。他既不放心群臣,也不放心太子。既然皇帝心中早有成算,他这么说,不过是顺着皇帝的意思罢了。事事以皇帝意思为尊,这也是他在李翊身边伺候多年,还屹立不倒的原因。
“这倒是老成谋国之说,不过……太子也需好好历练一番,朕这次就什么都不说了,只是看着他做吧。”李翊站起来,看了一下太子住处方向,说:“希望这次,太子不会令朕失望。”